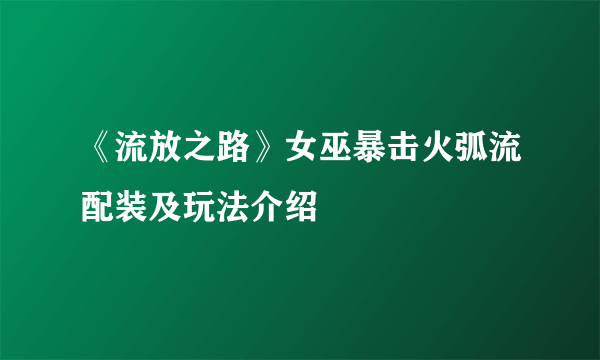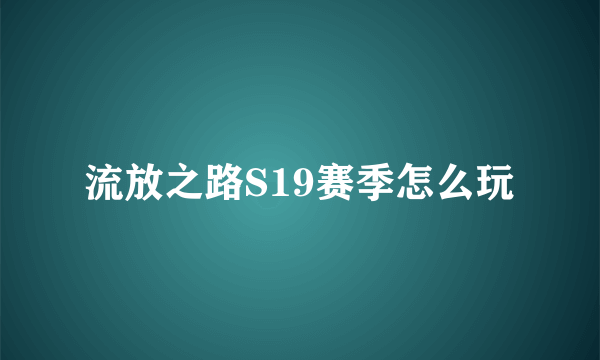屈原流放与沉江
的有关信息介绍如下:
这个问题也是屈原研究的老大难问题,历来说法很多很乱。而我根据新中国成立初期出土的《鄂君启节》,对屈原流放的路线以及沉江年代的问题有了一些新的看法。
我先简单地介绍一下《鄂君启节》。《鄂君启节》是楚怀王时的珍贵文物。“节”就是“符节”,是交通时所用的证件。这个“节”是鄂君的,他封在今天的武昌一带。鄂君是个贵族,他一方面要享受许多东西,用车、船搞运输;另一方面又要做买卖,当然是官商买卖。做买卖要走水路、陆路,需要交通证件,这就是《鄂君启节》。《鄂君启节》有两件,一件是车节,上面详细地记载着当时官商通行的陆路路线;另一件是舟节,也详细地记载着当时官商通行的水路路线。经过专家们的考证,认为这是世界上详记两千多年以前交通要道的唯一无二的珍贵实物。
新中国成立以来,专家们对《鄂君启节》做了许多研究。但是结合屈原当时流放的路线来研究,则是新问题。
关于《鄂君启节》的“舟节”,所记的水路地名、路线是这样的:
01
首先从鄂地出发,向西走,再溯汉水而上,直达汉北;
02
再从汉北折回,向东南,以长江为干线,一直达到江西的彭蠡一带;
03
又从彭蠡一带折回,往西南走,经过湘水、资水、沅水,一直到澧水,然后北上过长江,到楚都郢城。
总之,这是一个大的三角形似的水路路线。这三条干线,无疑是楚国在历史上所形成的东连吴、越,西通秦、蜀的国际通商路线。至于车节,则是东北与陈、蔡相连的国际路线。
我根据屈原的《九章》进行考察,发现屈原当时流放所走的路线,与“舟节”的路线大体一致。一般传统的观点说屈原当年流放之后,走的是很荒凉偏僻的地方,是漫无目的地到处流浪。但是将《九章》与“舟节”相比,我认为屈原当时走的是通商大道,并没有流窜于山野小路。他往往走到一个地方要住一段时间。例如西北他走到汉北,西南他走到溆浦,这两处都是当时楚国的边境要塞,都是跟秦国接境的地方,是楚国的边境重镇。屈原在这两个地方住了一段时间。
而且,屈原首先走的是东方,到了江西的泸江、陵阳一带。那儿是楚国的大后方,当时吴、越两国已经被楚国灭亡了。如果屈原想在流放期间平安地度过一辈子,这个地方是最平安无事的了。但是,屈原并没有这样做,他并没有贪图安全,他先跑到了汉北,后来又跑到溆浦,专门跑到这两个与秦国接壤的地方去。
这些事是值得我们认真思考的。
刚才我说了,屈原在顷襄王时被放所走的路线与《鄂君启节》大致是一致的。但是也有所不同,不同在于:他走的路线的先后次序与《鄂君启节》不同。屈原所走的路线是这样的:
(1)《鄂君启节》是先走汉北;而屈原离开郢都后,先走的是东方。他沿江而下,到达了泸江、陵阳一带。这个原因很简单。顷襄王元年,秦国兴师打楚国,战事发生在丹淅,就在汉北,今湖北省的北部。楚国打了败仗,死了几员大将。边关吃紧,首都震动。所以当时屈原被放,就与百官和民众一起沿江而东下,一直走到了陵阳。这就是《九章·哀郢》里所说的“当陵阳之焉至”,即是说我走到了陵阳又往哪里走呢?其后屈原基本上停下来了。后来过江到了泸江一带。
(2)《鄂君启节》从汉北南下,又以长江为干线,向东一直走到彭蠡,然后又转折而向西南,到湘水、资水、沅水、澧水。而屈原在陵阳住了九年之后,他又顺着当时的官商水路,溯江而上,溯江北而行,直达汉北。然后又沿汉北而下,西南溯沅,直到溆浦。在溆浦住了几年,又向东走,过了资水、湘水,到达了汨罗江边。屈原走的路线也是一个三角形。
现在我们来考察一下屈原为什么溯汉水而到汉北和为什么南下到溆浦的问题。
首先讲一讲屈原到汉北去的问题。
屈原流放到泸江、陵阳一带后,并不安心于苟且偷安。作为一个爱国主义者,他每时每刻都关心着国家的事情,关心着国防前线,所以他要到汉北去。另一方面,我们从屈原的作品来看,他在《哀郢》中说“至今九年而不复”,他痛心于不能回到首都去。当时楚国是一批卖国者掌权,他自知回不了首都,于是想到了楚国先君所住过的地方。《哀郢》结尾有这样两句诗:“鸟飞反故乡兮,狐死必首丘。”鸟儿要飞回故土,狐狸死了头也要朝着故土,这种感情是多么强烈!屈原在陵阳住了九年,写了《哀郢》,抒发了自己这种深沉的感情。这绝非泛泛的抒情之笔。
但是,他回不了郢都。那么他返回到哪里去呢?
我们知道,楚国的首都曾多次迁移。楚怀王时是在郢,但是在楚国都郢之前,楚国的首都是在丹阳。
丹阳具体在什么地方,现在学术界还有争议。但是其方位一定在丹淅的北面,丹水、淅水的北面,就是在汉北。近年来,在丹阳发掘出了楚国的公子午的墓。公子午是春秋时楚国的人,当过宰相,《左传》里多次提到他。公子午的墓中发现了一些鼎,有一件是《王子午鼎》,所以知道这个墓是公子午的墓。但是,公子午死于楚康王八年,那时楚国早已经以郢为首都了,为什么公子午死于郢而又葬于丹阳呢?郢都和丹阳,相距千余里。公子午的迁葬,当是古人“归葬”的遗俗。丹阳是楚国的旧都嘛。古代民族迁移,死后多归葬故地,因此,北魏孝文帝犹有“迁洛之民,死葬河南,不得还北”的规定。
同学们读过《礼记》,其中有这样几句话:“太公封于营丘,比及五世,皆反葬于周。”意思是说姜太公封到齐地,传了五代,死一个就归葬一个到陕西老家去。所以《礼记·檀弓上》在记载了这一史实后说:“乐,乐其所自生;礼,不忘其本。古之人有言曰:‘狐死正丘首,仁也。’”可以看出,古人把“归葬”与“狐死首丘”联系在一起。所以,屈原当时知道自己不能回到郢都,那么,也应当像“狐死首丘”那样,回到故都去。
当时屈原流浪陵阳九年之久,无时无刻不在怀念着郢都的“州土之平乐”“江介之遗风”。但事与愿违,在顷襄王执政,群小擅权之下,赦免既不可望,归郢自不可能,因而先烈陵墓所在的汉北丹阳废都,也竟成了他向往的目的地,从而发出了“鸟飞反故乡兮,狐死必首丘”的悲叹。他才决定走向汉北,希望能够瞻仰先烈的遗迹,借以抒发其怀念故国之忧思。这就是《哀郢》的“狐死必首丘”跟次篇《抽思》的“来集汉北”的内在联系。屈原的流亡路线,如果说开始的东走陵阳是由于战局失利所导致,那么这时的“来集汉北”,则是由于思念故国的强烈感情所驱使。
所以说,屈原到汉北去,感情上是很复杂的。从当时的政治形势来看,他想到汉北去;从屈原的民族意识来看,他也想到汉北去。他要去看一看国防前线的情况,也要回到丹阳旧都去。汉北丹淅一带,已成楚国的边疆要塞,为秦楚交战的必争之地。据《史记·楚世家》说:楚怀王十六年曾受秦国商於六里之骗。这个“商於”即在丹淅附近。《楚世家》又云:怀王十七年春,“与秦战丹阳,秦大败我军,斩甲士八万,虏我大将军屈匄”。而《屈原列传》则讲:怀王“大兴师伐秦,秦发兵击之,大破楚师于丹淅,斩首八万,虏楚将屈匄”。可见丹阳即丹淅一带。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楚世家》又云:楚顷襄王元年,秦拘怀王要地不得,竟“发兵出武关,攻楚,大败楚军,斩首五万,取析十五城而去”。《正义》引《括地》谓楚析邑“因析水为名也”。是析即丹淅之淅。可见,丹淅之地,除为楚先公先王的陵墓所在之外,又成了楚国西北的门户,并屡遭秦国的袭击。而且正当屈原被放离郢都赴陵阳之时,曾由于丹淅大败,危及郢都,人民离散。作为爱国主义者的屈原,即使身遭流放,对此也决不会淡然忘却。我们从《哀郢》中所说“外承欢之汋约兮,谌荏弱而难持”看来,他对顷襄王为了“承欢”暴秦所实行的和亲软弱政策是极为忧虑的。屈原不远数千里由陵阳到汉北,绝不完全是为了聊慰故国之思,而且隐然有关心祖国安危,观察边疆动态的曲衷。《史记·项羽本纪》说:“楚南公曰‘楚虽三户,亡秦必楚也’。”“三户”,据说就在汉北一带。
以上简略地解释了屈原为什么要从大后方的陵阳转向汉北。
第二,我们讨论一下屈原又为什么要从汉北沿汉水而下,走向西南,到了今天湖南省西部的溆浦一带。
溆浦在沅水边上,溆浦这地方我去过。溆浦那时属于楚国的黔中郡,是与秦国接壤的西部边境。据《史记》说,秦国一直想要那个地方。所以屈原一直不放心,就从汉北跑到溆浦去。他从楚国的西北国防前线一直跑到西南的国防前线,在那儿住了几年。我前几年到那儿去的时候,专门到文化馆去问了一下,询问现在还有没有屈原的古迹。文化馆的同志说现在没有,但是离县城几十里有一个大队,水边上有一座亭子,当地老乡说屈原在那儿乘过凉。因为天黑了,路又远,我就没去了。老乡们口耳相传屈原到过溆浦,这是符合屈赋所说的内容的。
屈原流亡西南的原因:传统的说法,以为屈原当时是被放于“江南之野”,但我们从整个《九章》来看,其说并不可靠。盖顷襄王时屈原被放在外是事实,但并没有规定他必须住在哪里。因而,除了《哀郢》描写开始出发是迫于当时战局,不得不跟流民一起东下而外,其余的行踪,都是由他自己决定,有他自己的想法的。前面所谈屈原远抵汉北的情况是如此,而这次西入溆浦,同样是如此。
据《史记·楚世家》:怀王三十年,怀王用子兰之言,北会秦王于武关,被拘于秦,“要以割巫、黔中之郡”。怀王不许,结果病发而死于秦。就在秦要怀王割“黔中”的第二年,即顷襄王的元年,屈原即被放。作为具有强烈爱国感情的屈原,对此后黔中的命运如何,绝不会恝然忘怀。因此,他之由西北与秦接壤之汉北国境转到西南与秦接壤的溆浦国境,绝非没有目的。因而他转到西南,不去别处而远及黔中边界,同样是为观察边疆动静的爱国心情之所驱使。
从战国时期楚国与秦国的关系来看,所谓“纵则楚帝,横则秦王”,确实是如此。但自怀王时屈原被疏以后,纵势已破,楚国渐弱。尤其是怀王二十四年,秦昭王初立,与楚和亲;第二年楚又与秦盟于“黄棘”。自此以后,楚国国势,一蹶不振,处处被动,每战必败。不难看出,作为外交政策,“黄棘之会”,是楚国由强到弱的转折点。屈原到了西南国境,想起了外交失策的往事,故在《悲回风》里写道:
借光景以往来兮,施黄棘之枉策。
求介子之所存兮,见伯夷之放迹。
洪兴祖《楚辞补注》对“黄棘”之义,不同意王逸的曲解,而主张指怀王二十五年的“黄棘之会”,这是对的。介子之有功于晋文而被遗忘,伯夷由于不食周粟而被饿死,这些前人的往事,怎能不引起屈原想到在国家危亡之际的自处之道呢?
据史载,公元前278年,秦军攻下了楚国的首都郢都。第二年,公元前277年,秦军又攻下了黔中郡、巫郡。巫郡是屈原老家秭归所在地。屈原很可能就是在黔中郡失守之后离开溆浦,又向东北方向走,到了汨罗江边,投江而死。
这儿有一个问题:屈原之死,如果说只是为了殉国而死的话,那么在楚国的首都陷落时,他就会死在溆浦。为什么还要往东走,去死在汨罗江里呢?这儿有几个原因:第一,楚国郢都被攻陷的第二年,秦国又攻打黔中,他是不得不往内地走了。第二,屈原在郢都陷落之时,复仇之心未死,希望之心未灭,他也需要到内地来看一看,观察楚国的情势,所以到了长沙。然而,楚国的情势一塌糊涂,可以说是大厦倾倒,土崩瓦解,楚王率领百官狼狈逃往陈。屈原看到国家这个样子,所有的希望都破灭了,所以投汨罗江而死(从当时的战局来讲,无疑是殉国;但从作品内容来看,毋宁说是殉道、殉志)。
汨罗江畔,乃古罗子国故地。今年(1983)中南五省考古队,在这里发现古罗城遗址和很多战国至西汉墓葬,出土很多楚兵器和楚文物;有几十座大墓,墓主身份是较高的。可证长沙乃至罗城一带,乃战国时楚南的政治、文化、经济、军事的重镇,并非荒凉之地。则屈原的东北走长沙,并徘徊于汨罗,是有目的,并非信步流亡。
以上我对屈原之死的讲法,与过去的人有所不同。他们认为在郢都陷落时,即公元前278年,屈原就死于汨罗江。这个观点是郭沫若同志1953年提出来的。当时世界和平理事会纪念屈原逝世二千二百三十周年,就是用的郭沫若同志的说法。去年(1982)在湖北秭归开了个学术讨论会,纪念屈原逝世二千二百六十年。但是根据我的推测与考察,屈原是公元前277年逝世的,所以今年(1983)才是他逝世二千二百六十年忌。
以上我讲了屈原在顷襄王时被流放所走路线以及他沉江年代的问题,我为此写了一篇文章,论据相当详细。这儿只是讲其大意。
点击名片 关注我们